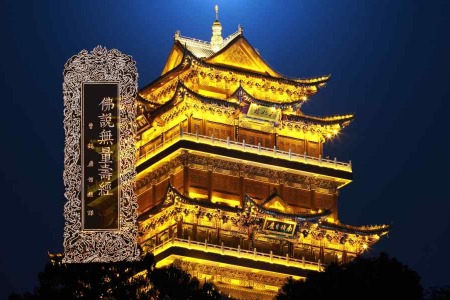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的热播,让许多人重新看见了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五代乱世、开创大宋基业的雄才大略。但历史中的赵匡胤,不止有“一条杆棒等身齐”的武略,还有着另一面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形象——一位深思熟虑,并将佛教作为重要治国方略的护法国君。
这种“护法”,并非简单的个人迷信,里面有很深的现实考量。赵匡胤亲身经历了后周世宗柴荣大规模的“毁佛”运动。世宗为筹军费,曾亲手劈裂百姓认为极有灵验的镇州大悲观音铜像。这让赵匡胤内心受到很大震动,他曾私下问高僧:“自古有毁佛天子乎?”得到的回答是: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皆因毁佛而国祚短促,不得善终;周世宗毁佛,亦未过五年便染病身亡。这话点醒了他,他感叹道:“毁佛法非社稷福。”
所以,当他建隆元年(960年)黄袍加身后,做的第一件文化大事就是拨乱反正。他下诏保存未被完全毁坏的寺院,允许民间佛像移往安全处供奉。同年,他为庆贺自己的“长春节”,下令普度天下童行八千人出家,发出了明确的复兴佛法的信号。他做的很扎实:恢复“试经度僧”制度,防止滥竽充数;在益州(成都)组织雕刻中国第一部官刻大藏经《开宝藏》;甚至派出一支157人的庞大僧团,远赴西域(印度)求取佛经。
他还有句很有意思的私语。宰相赵普见他读《金刚经》,他便嘱咐说:“不欲甲胄之士知之,但言常读兵书可也。”这话泄露了他的真实想法:在他看来,佛法劝善止恶、安定人心的力量,是一种更高明的“心法”,能“阴翊王度”(暗中辅助王化),其效果比单纯的武力威慑更长久。他曾对赵普说:“佛氏之教有裨政理,普利群生。”他甚至在扬州战场旧址建寺超度亡灵,将领因放生而受到他的赞叹。这些都是在用佛法的精神,化解乱世留下的戾气,重新凝聚人心。
几乎在同一时期,东南还有另一位国王,在用另一种方式做着类似的事,那就是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,钱俶。
钱氏世代信佛,到钱俶时达到顶峰。他仿效古印度阿育王的故事,铸造了八万四千座小铜塔,内藏经卷,散布境内。但最关键的,是他做了一件“文化抢救”的大事。
当时,天台宗智者大师的核心著述,因唐末五代的战乱,在中原已残缺不全。高僧羲寂(即天台宗十五祖净光尊者)为此痛心疾首,钱俶闻知后,当即决定:派遣使者携带重礼,渡海前往高丽、日本,访求失落的教典。
这是文明存亡之际,主动伸出的求援之手。后来,高丽僧人谛观携大量天台章疏来华,义寂法师得以在螺溪(今浙江境内)大弘教法,再传至四明知礼大师,天台一宗由此中兴。追根溯源,钱俶此举,功不可没。他后来归顺北宋,随身带入汴京的“释迦真身舍利塔”,震动朝野,仿佛也象征着这种文化血脉的回归。
这样看下来,赵匡胤和钱俶,一个在北,一个在南;一个以开国皇帝的果决手腕为佛法开拓生存空间,一个以地方国王的虔诚之心为文明续接智慧血脉。他们身处同一个破碎的时代,却用不同的方式,守护着同一种东西。
赵匡胤的护法,带着清醒的政治计算,是把佛教作为安定社会、教化人心的“软实力”。而钱俶的求经,则更接近一种对文化本身近乎本能的珍视与挽救。他们的动机或许不尽相同,但结果都是让那些险些熄灭的灯火,重新亮了起来。
《太平年》里演的,是权力游戏中“太平”的来之不易。而历史中这些君王无意中留下的痕迹,却告诉我们另一种构建“太平”的可能——它不在于城郭有多坚固,而在于人心的秩序与文化的光亮能否被妥善安放,并穿越时间。
千年前的帝王将相,早已化为史书里的几页墨迹和荧屏上的影视剧集。但他们守护过的那点星火,却穿过乱世的烽烟,依然在某些时刻,照亮后来者的案头与心田。这或许就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:它留下的不只是成败兴亡,还有这些关于文化存续、关于心灵安顿的,柔软而长久的回响。
惭愧后学·持心于麒麟湾闲居
2026年1月31日 腊月十三